我已多久沒再翻閱太宰治?住在林雙家裡時,我將書櫃上的村上龍補齊了大半,村上春樹也補上了一本,原以為他想走向開放式關係,於是買了許多類似思想的書,但其實他不看。
我們看書的分歧點就像我從青春期走向成人的分類,而他仍然著迷著某人某事某物。
翻閱自己20多歲的舊blog曾寫道
一個人沉迷於什麼看他的書櫃便略知一二,那不僅僅是多年的蒐藏也代表一個人平常被什麼攝住。
翻了第一頁便笑了出來,用了但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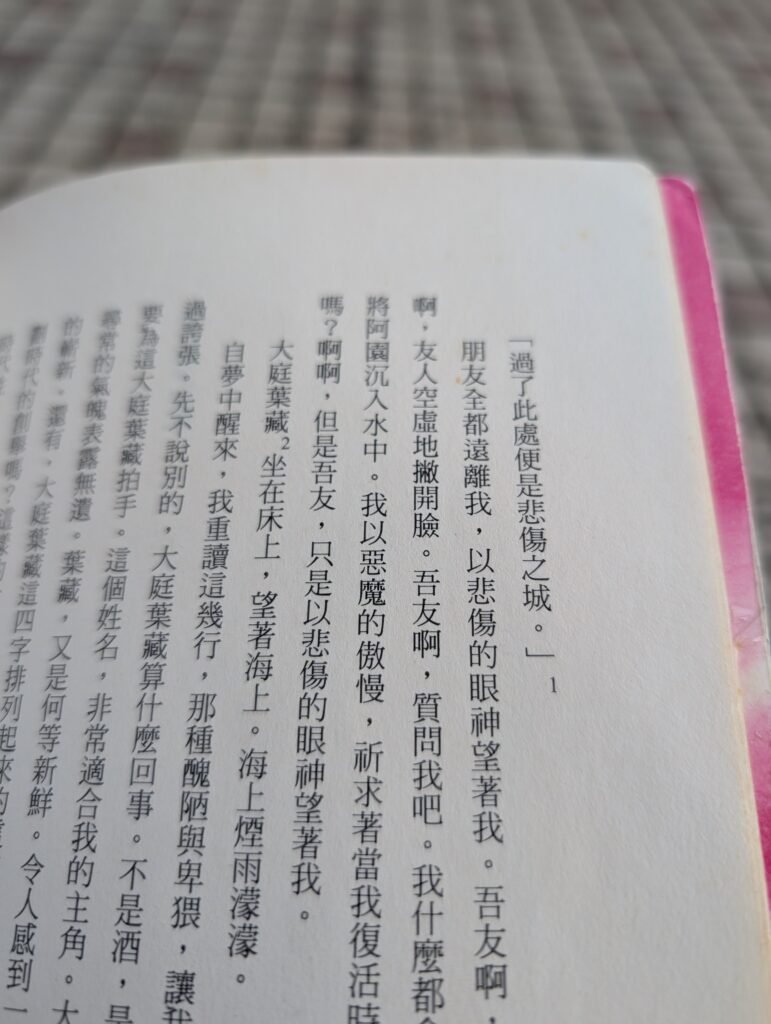
二十多歲的文字,人們常常說我像太宰治那樣,無病呻吟卻又吸引人。
若不是在信義區浪蕩多年,喜歡那樣沉迷於肉體與報復心作祟,一邊享受著辱罵一邊享受著愉快,不會知道自己變態程度有多高。
我與S的拉扯維持了好些日子,他每次氣憤來到松仁路的住家,跪在地上一邊幫我收捨整理,一邊嘴裡不饒人的問著到底是誰出賣我。
沒有人出賣你,其實,是你自己行為太過頭而展現的太明顯甚至整個軌跡都呈現在他人眼前,有心之人勢必會送來我眼前,畢竟我也長得不差,你有許多對象你的對象中的對象卻也因為憐憫我而靠近我。
出賣你的是你自己。
我總是說反正我就是知道了。
他總會氣到關門離去,在離去前把我安置好,偶爾陪我入睡,我總看著他的背影,我一直都看著任何人的背影,被他們怪罪被他們責備被他們摟著抱著吻著說著昧著良心的話,我從不如他們的心,我會演給對方看,他們想要我的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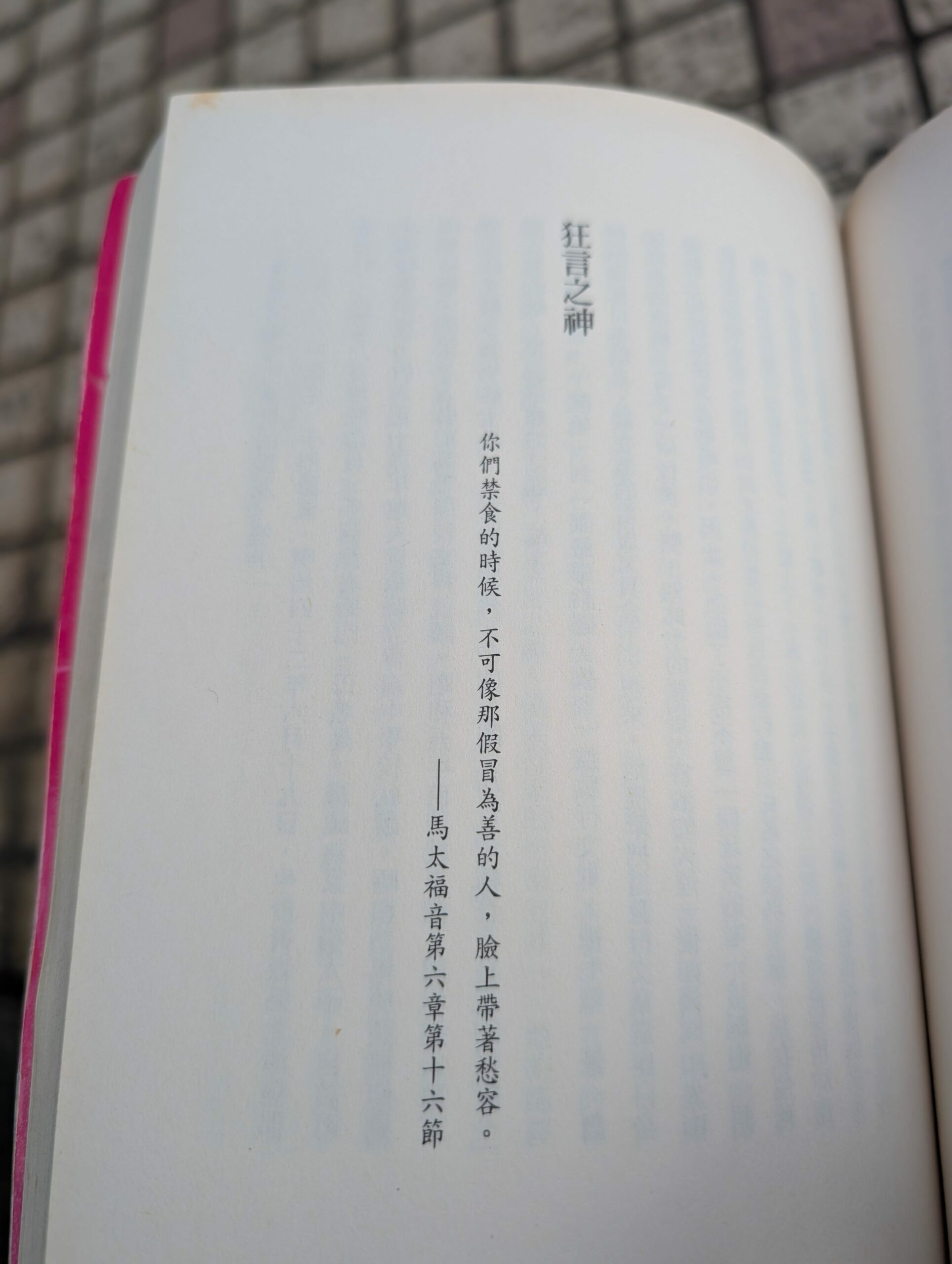
因為他們喜歡如此,於是我更喜歡玩弄他人嗎?
這些天我睡得很好,老白問著我的睡眠。
從我住進那家我鮮少陷入沉睡,總是會醒著在黑夜中聽著對方的囈語呢喃甚至偶爾會故意與他對話,我看著他背影聽著他呼吸聲,偶爾我會鑽入他的懷裡一會便又走去陽台,客廳待上一陣子。
直到我毀滅,才帶來的寧靜,我終於可以好好睡覺緊挨著沒有溫度的靈魂。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平靜。
哪怕我說著想要肯定想要什麼,不,我其實最想知道的是從一開始的離開,你要的是什麼?
但我好像知道答案了。
於是我說我從來不能控制任何人,想掛掉就掛掉吧。
對於一個已不花時間溝通,總要隔天再說甚至沒有心的人,任何話語都已沒有意義。
一份工作的dateline就是在那,延期交不出來就是有問題,是產能不足還是資金問題甚至根本沒生產的只交出一張空頭支票,都有可能。
我不願去臆測,正如同回到台北,我每天唸書工作跑行程上健身房的日復一日,我體態正在改變,小弟其實沒有大哥說的那麼沮喪,我是他們的希望,我只能拼命發光。
我仍然會幫忙,在林雙真的陷入萬劫不復之時,哪怕是地獄門口,我都會親自走一遭。
這是我的諾言,就像貓說他死前會打給我一樣,我要在病房裡與他做最後一次。
我會到墳前自慰給他看,我會做這些我們說過的任何自我調侃的話,因為我很認真,人生不認真面對就是枉然。
認真的面對自己的情慾流動認真的面對人性的貪婪認真的面對人性被自己垢病的一切。
我是爛但我也有底線。
我想怎樣便怎樣是建立在不妨礙他人自由意識下的我想怎樣便怎樣。
我是這麼想的。
一如往常的唸完楞嚴咒,走到早餐店,點一份物美價廉又好吃的小籠包與鹹豆漿。
想起去金門吃的花生湯與金門油條,而愛上,原本想去忠貞市場買,但現在大概也無法再踏入那些地方。

老闆夫妻手上各自有一圈墨線,當我回來住時發現了這家過去幾年都沒來過的豆漿店,我問著老闆娘妳們有情侶刺青耶,老闆娘笑著說那是我先生。
我也曾想跟誰有一對的紋身,一對的,最後我只想把我右手包上同樣的骷髏男士,我自己給我自己就好了。
我一坐進來店裡,原本只有老闆一家在嬉戲的安寧,小女兒說著要去買鮭魚也提到店內營業金額,說著說著老闆突然說了一句幹話妳全家都有問題,老闆娘說妳也是她家人啊,而三個人笑起來,站在櫃檯的我也跟著笑出來。
我也曾想要與對方有一個店一個家一位屬於我的孩子,我想要過這樣安靜平靜的日常,再難熬也會因為笑聲不斷而雨過天晴,再辛苦也會因為對方一個笑容而褪去疲倦只剩歡喜。
漸漸的人群突然聚集起來店裡瞬間塞滿人,我放在桌上的小丑之花,每個人走過去都低頭看了幾眼。



發佈留言